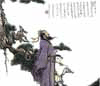一位中年男子身著白色襯衣、灰色西服端坐著,頭發(fā)一絲不亂,戴著眼鏡的雙目炯炯有神,左手很隨意地放在胸前,摁住西服的兩邊,這是旅法畫家潘玉良創(chuàng)作的肖像油畫。畫中的男子源于生活中的真實人物,他叫蔣恩鎧(1904年-1999年),祖籍太倉,成長于常熟,與“月季夫人”蔣恩鈿同宗。
蔣府少爺迷藝術
蔣家是太倉的名門望族,蔣恩鎧的父親蔣汝圻,字仲京,先后娶過五房妻子,原配汪氏并無子嗣,續(xù)弦廖氏生了長子蔣恩錫(字用藩)。按迷信的說法,蔣汝圻的命比較硬,四房妻子先后離世。第五位夫人王仁采是常熟人,即蔣恩鎧的母親,王氏為人能干,性格剛強。王仁采的美好生活才開始不久,蔣汝圻卻走了,蔣恩鎧尚在母腹,青年喪夫的打擊太大了,但她跨過了這道坎,獨自撫養(yǎng)兒子長大成人。年輕寡婦帶著遺腹子的生活必然辛苦,何況大家庭的關系比較復雜?;蛟S沒有適應太倉的生活,王仁采帶著年幼的蔣恩鎧回到常熟,她親自覓地造房,在言子橋旁的班巷建造了三棟相連又獨立的小洋樓,這是大手筆,在當時的常熟城里煞是風光。蔣恩鎧就在這大院里長大成人,結婚生子??上У氖牵@座王仁采費盡心血打造的蔣家大院在抗戰(zhàn)爆發(fā)之初就被日本的炮彈炸毀,連兒媳李淑香的豐厚陪嫁也化為灰燼,炸剩的半個花廳后改造成了小房子。
蔣恩鎧母子偶爾也回太倉老宅看看,然常熟無疑成為蔣恩鎧的第二故鄉(xiāng)。蔣恩鎧素有三少爺之稱,工作之后同事戲稱蔣三爺,家譜記載只有一個哥哥蔣恩錫,據蔣恩鎧的女兒蔣曼美分析,他上邊可能有一個夭亡的姐姐。蔣恩鎧在嚴母的管教下,逐漸長大,17歲就外出求學,讀中學時就寄讀,緊接著在南京的一所政法大學完成學業(yè)。蔣府的豐厚家財,為其成長提供了充足的物質保障和優(yōu)良的學習環(huán)境,據說常熟老宅有一間房子專門收藏了他鐘愛的樂器。不遠處的太倉蔣家大院,每年要舉行兩個月的曲會,邀請名角演出,當地士紳也來欣賞客串。蔣恩鎧從似懂非懂起,就聽慣了纏綿悱惻的昆曲,也慢慢愛上了昆曲,跟著大人們學習,他的一副好嗓子引起了陳道安的注意。
陳道安(1878年-1957年),祖籍江陰,長于京城,秀才出身,拜梅蘭芳的伯父、皮黃音樂演奏家梅雨田為師,學習胡琴,聽遍京劇名藝人的唱腔,時稱“海內四大胡琴圣手”之一。1900年,陳道安來到常熟與趙家千金成婚,自此將京劇帶到古城。他熱情點撥常熟的京劇票友,有時親自操琴,幾次合串京劇傳統(tǒng)劇目《洪羊洞》。1923年起,陳道安定居常熟,先后倡立“中音俱樂部”、“虞聲友社”等,為當地人所稱道。陳道安親自教蔣恩鎧唱青衣,一個精心傳授,一個認真學習,蔣恩鎧就這樣與京劇、昆曲結下了不解之緣,且成為他一生的嗜好與寄托。
縱觀蔣恩鎧的人生道路,貌似與藝術一點也沒有關系,輾轉各地做外交官,但忙碌的公務并沒有影響他對中國傳統(tǒng)戲曲藝術的愛好,從年少到白頭初衷不改。退休后定居臺灣的蔣大使仍然以京劇、昆曲自娛自樂,陶冶心情,但他對友人說,現在年紀大了,不好意思唱青衣,唱小生倒還可以。
論文《昆曲》揚海外
1927年大學畢業(yè),蔣恩鎧打算到日本留學,因為日本剛好發(fā)生大地震,母親擔心他的安危,否定了他的想法。到第二年,幾個同學正好要到法國留學,于是他們結伴同行,先補習法語,再到法國巴黎大學攻讀文學。到法國留學似乎有點盲目,然藝術之都巴黎的氣質倒與蔣恩鎧的藝術追求十分吻合。在一次家庭聚會時,人們問他為何到巴黎留學,他脫口而出“有趣”。1929年,他的妻子李淑香來到巴黎陪讀,照顧他的生活。
蔣恩鎧的時代,昆曲代表了高雅藝術,也代表了一種文化坐標。江南的世家子弟都好這一口,如九如巷的張家姐弟,怡園的顧公可、顧公碩昆仲,補園的張紫東等,都癡迷昆曲,都能上臺表演一番。在巴黎,他認識了王寵惠的高足、蘇州人徐公肅,一位昆曲愛好者,兩人一見如故。徐公肅建議蔣恩鎧的博士論文以昆曲為題,并對他說:“只有你懂昆曲,別人不懂,所以寫昆曲最好,別人考不倒你?!边@顯然有點走捷徑,主意雖好,但在當時的巴黎,找不到昆曲的資料,論文從何寫起,蔣恩鎧只好求助于家人。當一箱有關昆曲的圖書資料漂洋過海來到巴黎時,他的心情一下子輕松許多。自幼浸淫于昆曲,也能與票友們同臺演唱,但要從理論上進行研究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情。他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自修昆曲理論知識、研讀劇本,有時睡到半夜想起某個問題就起來寫,終于寫成博士論文《昆曲》,這是他一生最耗心血的事,也是中國第一本向法國人介紹昆曲的專門論文。1998年,蔣恩鎧對朋友說:“這輩子最辛苦的不是辦外交而是寫論文?!?br> 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葛蘭言(Marcel Granet 1884年-1940年)是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漢學家,曾到中國實地考察兩年,之后又被法國外交部派往中國一年。葛蘭言通過研讀大量的中國古籍,又對中國進行近距離考察,運用社會學理論及分析方法致力于中國古代的社會、文化、宗教和禮俗的研究,而中國古代宗教是其研究的重點。這位中國通師從著名漢學家沙畹,是其門下四大弟子之一,與當時另一位漢學家伯希和齊名。在巴黎讀書期間,蔣恩鎧與葛蘭言交往密切,老師對其關照有加,而他也為老師校勘出版文稿。七十多年后,蔣恩鎧回憶葛蘭言教授時,依然充滿感激與欽佩,說老師查中國字典,比中國人還要快。除了葛蘭言教授對其論文進行指導外,還有一個朋友為蔣恩鎧抄寫了論文中的部分曲譜,他就是當時在里昂工作的上海人陳雄飛?!独デ分皇顷愋埏w與蔣恩鎧結緣的開始,之后兩人一起活躍在國民黨政府的外交舞臺上,無論工作關系還是私人交往,他們交情彌篤。1990年陳雄飛八十大壽之時,蔣恩鎧與朱女士合唱了一段《霸王別姬》,年過八旬的蔣恩鎧把霸王項羽那種蒼涼的心境盡情抒發(fā)出來。想當年他們先后到法國留學,一個學的是文學,一個學的是法學,卻殊途同歸,都從事外交工作,而今都已步入暮年,演繹的是項羽的無奈,卻透著蔣恩鎧的豁達氣概。
1932年11月8日,蔣恩鎧獲得巴黎大學文學院博士學位,而論文《昆曲》于1933年獲得巴黎大學中國學院的資助得以出版。有意思的是,2003年蔣恩鎧的外孫女錢家璧的丈夫無意中發(fā)現這篇論文被收錄在百科全書《音樂史》“中國經典音樂史章節(jié)”中,且被多所法國大學的圖書館及美國普林斯頓等世界名校收藏。幾經尋找,靜靜地躺在法國一家古老的小書屋(Orientaliste)的《昆曲》重新回到蔣家后人手中。
此生只為昆曲醉
有位記者曾經對蔣恩鎧開玩笑,說他如果唱昆曲說不定比做外交官名氣大。雖是笑話,但道出了蔣恩鎧在藝術方面的造詣及對戲曲藝術的執(zhí)著。
在法國留學期間,作為一名中國留學生,蔣恩鎧在巴黎的魁末特博物館舉行過幾次音樂會,表演中國戲曲和胡琴,宣傳中國音樂與戲曲藝術。留法期間,他的才藝在同學中廣為傳播,大使館每次舉行晚會,十個節(jié)目,蔣恩鎧要承包六個,還經常要為人操琴伴奏。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委托他教人吹笛,他還教外交官夫人們唱《禮運大同篇》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為公…”1933年,程硯秋訪問法國等歐洲國家,宣傳國粹京劇,蔣恩鎧得知后,抓住機會,專門到旅館拜訪程硯秋。
1936年,蔣恩鎧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工作后,有更多機會接觸各種人物,參加昆曲雅集。中華書局樓上的客廳是他們同期唱曲的首選地,錢昌照夫婦也是昆曲愛好者,錢昌照是常熟人,與蔣恩鎧算是半個老鄉(xiāng)。公務之余,以曲會友,相聚一堂,不亦樂哉。在南京,蔣恩鎧結識了蘇州人吳梅,吳梅以戲曲理論家、教育家的身份聞名學界,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戲曲方面的人才。秦淮河的酒館中,蔣恩鎧數次遇到酒量驚人而喜歡豪飲的吳梅,每每喝高的吳教授總要發(fā)牢騷,發(fā)完牢騷,還要哼上幾句昆曲。年輕的蔣恩鎧覺得吳梅喝酒太多,把嗓子喝壞了,音質受到影響,所以昆曲唱得不怎樣,但他肯定吳梅的學問做得好。
蔣恩鎧出使法國時,顧維鈞大使舉辦活動時,經常把在里昂的蔣恩鎧召到巴黎,不是唱昆曲就是演京劇。由于吹笛子的人難找,后來蔣恩鎧只能放棄昆曲,表演京劇。
昆曲是文化人的“古典音樂”,但在大陸一度銷聲匿跡,而臺灣那頭余音不絕,那些無法回到故國的人以昆曲消磨歲月,寄托情思。當疏離了很多年的兄弟再次牽手時,海峽兩岸一起吟唱著故國的天籟之音。1997年6月23日,昆曲表演家計鎮(zhèn)華、梁谷音到臺灣開展文化交流,特地拜訪了90多歲的蔣恩鎧,他們暢談著昆曲在兩岸的流傳及未來如何發(fā)揚這一傳統(tǒng)藝術。
少小離家老大還
1924年,蔣恩鎧與比他小兩歲的李淑香結婚,由于蔣家與李家都是常熟城里的大戶人家,因此婚禮異常熱鬧,持續(xù)了兩周。當年李淑香的嫁妝長達一條街,引來市民們的觀看。蔣恩鎧夫婦相愛一生,相互扶持一生,他們共生育九個孩子,五個長大成人。除安立是兒子外,其余都是女兒,而今分別生活在美國、法國和中國。照理蔣恩鎧的兒女輩屬于憲字輩,但由于父親的洋派,孩子們都沒有按族譜的規(guī)定取名,他們分別叫麗琳、蜜琪、曼美、芳西、安立。
三女兒蔣曼美出生于1930年8月25日,父親那時還在法國,1934年回國見到的蔣曼美已是四歲的漂亮娃娃了。對蔣曼美來說常熟才是她的故鄉(xiāng),她自幼跟隨祖母,生于斯、長于斯、工作于斯,講一口地道的常熟話,一輩子住在老宅,守護著最后的家園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,蔣恩鎧從重慶回到老家,探視母親和孩子,此時的蔣曼美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。新中國成立前夕,蔣曼美在學校參加地下黨組織的外圍活動,迎接光明,之后參加共青團,而蔣恩鎧遠在法國。直到1992年,蔣曼美到臺灣探親,骨肉離別四十余年才得以相見,少女已是六旬老嫗,雙親則是耄耋之年,歲月在親情面前顯得那么蒼白,任憑多少年的分離也消磨不了藏在心底的企盼與思念。三年后,蔣恩鎧回到大陸探親,此時李淑香已離開人世。親人的團聚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喜悅,故鄉(xiāng)的美食更是真切難忘,蔣曼美說父親最愛吃大閘蟹和虞山上的松樹蕈,這是久違的故鄉(xiāng)味。
蔣恩鎧與蔣恩鈿是遠房堂兄妹,偶爾有聯系。1950年,遠在美國學習考察的蔣恩鈿獲悉新中國成立的喜訊,立即帶著一雙兒女回國。他們從美國上船,經加拿大,取道歐洲,看望駐法的蔣恩鎧。堂兄妹因個人經歷不同,對時局的看法也不盡相同,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之間的親情交融,在巴黎的幾天,蔣恩鎧每天派車陪他們游覽巴黎的名勝古跡。1994年,蔣恩鈿之子陳棣到臺灣辦事,特地拜訪了蔣恩鎧這個遠房表舅。四十多年未見,當年九歲的陳棣已年過半百,蔣恩鎧感慨萬千,別時容易相見難。
“父母在,不遠游”,但蔣恩鎧早年離家讀書,而后在外工作,漂泊在世界各地,沒有對母親盡到孝心,這是他的痛。之后,一條淺淺的海峽分離著兩岸的親人,法國成為他與常熟老家聯系的中轉站?!拔母铩北l(fā)前,他多次從法國寄回全家照,其實這全家照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家福,少了母親,少了三女兒。望著兒子兒媳與其他在海外的孫兒孫女,王仁采內心略感寬慰,但她等不及兒子回家的那一天就于“文革”初期離開了人世,盡管她已九十余歲,總有一絲遺憾在心頭。數十年后,蔣恩鎧終于踏上故鄉(xiāng)的土地,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虞山祭掃母親。他告訴兒女們,自己過世后,一定要陪伴母親。而今,他的孩子們將父母安葬在祖母墓旁,離開故鄉(xiāng)半個多世紀的游子不再遠行,靜靜地長眠于故鄉(xiāng)的青山綠水間,這里是他的家園,這里有他的母親。
□沈慧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