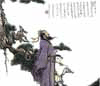□白 金
范伯群先生在《中國市民大眾文學(xué)百年回眸》這本書的開端,先提出了一個文學(xué)史上的重大問題:中國在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時段為何沒有市民文學(xué),特別是面向中下層市民的市民大眾文學(xué)?
蘇州在明清兩朝是一個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都市,不僅商貿(mào)發(fā)達(dá),而且手工藝精湛,是當(dāng)時的時尚之都。市民勢力大大擴(kuò)展,新興的市民意識大為增強。市民意識也深深地滲透到文化領(lǐng)域之中。馮夢龍編纂和創(chuàng)作的《三言》就出現(xiàn)在這樣的氛圍中,馮夢龍堅定地強調(diào)他的小說“話須通俗方傳遠(yuǎn)”的規(guī)約,使中國的白話短篇小說步入成熟階段。因此,中國文學(xué)史中無一例外地稱馮夢龍為市民文學(xué)大家。
清末民初,農(nóng)耕文明的都市轉(zhuǎn)型為現(xiàn)代工商文明都市之后,市民社會發(fā)育得更健全了,可是中國為什么反而沒有市民文學(xué)了?范伯群先生在書中回答了這個問題:這其實是文學(xué)史書寫帶來的問題,市民文學(xué)并不是真的消失了,而是被某些文學(xué)史扣上了帶有貶意的“鴛鴦蝴蝶派”的帽子,有的文學(xué)史中更認(rèn)定它是一股“逆流”。將名稱這樣一“扭歪”,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時段的中下層市民大眾文學(xué)多年來就變得萬劫不復(fù)。范伯群先生研究通俗文學(xué)30多年,他認(rèn)為,優(yōu)秀和較優(yōu)秀的所謂“鴛鴦蝴蝶派”作品,都是“良性的通俗文學(xué)”,而決不是“惡形的庸俗文字”。他們以蘇州籍作家為主干,而這些作家又大多到近在咫尺的全國出版中心——上海,發(fā)揮自己的才能。
在這本書中,范伯群清晰地理出了一條中國古今市民大眾文學(xué)的發(fā)展線索。在《中國市民大眾文學(xué)的前天、昨天和今天》一文中,他指出:馮夢龍們所反映的是農(nóng)業(yè)文明下的古代都市生活及市民意識增強的圖景;鴛鴦蝴蝶派作家繼承了馮夢龍的衣缽,描繪的是現(xiàn)代工商文明大都會市民生活的面影,在這批被稱為鴛鴦蝴蝶派的作家的手中,他們將通俗小說的類型進(jìn)行了定型化,這也是他們在文學(xué)上的重要貢獻(xiàn)之一;而目前出現(xiàn)的海量的網(wǎng)絡(luò)類型小說與他們也有血緣關(guān)系,網(wǎng)絡(luò)類型小說是對類型小說進(jìn)一步發(fā)展與細(xì)化,是新世紀(jì)市民喜聞樂見的市民大眾文學(xué)。它以青春市民為主力,當(dāng)更具活力與潛質(zhì),隨著“網(wǎng)而優(yōu)則紙”、“網(wǎng)優(yōu)而觸電”,形成網(wǎng)絡(luò)、書刊和熒屏的“立體優(yōu)勢”,更廣泛地吸引大眾的眼球。馮夢龍們的木刻雕版——鴛鴦蝴蝶派的機械媒體——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的去紙張、去油墨化,乃時代的遞進(jìn)與科學(xué)發(fā)展的聯(lián)袂同步,三者構(gòu)成了古今“市民大眾的文學(xué)鏈”。
這些被稱為“鴛鴦蝴蝶派”作家的作品,除供給精神食糧使中下層市民在閑暇時間得到娛樂與愉悅之外,據(jù)歷史學(xué)家們的研究,在“鄉(xiāng)民市民化”的現(xiàn)代化工程中曾發(fā)揮過一定的作用。通過閱讀,在娛樂中可以懂得如何去融入都市生活,這才是真正的“寓教于樂”。歷史學(xué)家稱這些通俗小說是“鄉(xiāng)民市民化的啟蒙教材”。
本書中的《報人雜感——引領(lǐng)平頭百姓的輿論導(dǎo)向》,還論證了一個過去所未能詳盡闡釋的問題,那就是這些通俗作家,其中不少人都是報刊中副刊的主編,他們都自稱“報人”。在這些副刊上他們發(fā)表了許多雜感隨筆,這是老百姓真正看得懂的雜文。如周瘦鵑從1919年進(jìn)《申報》主編《自由談》約12年之久,嚴(yán)獨鶴在1914年就進(jìn)《新聞報》主編《快活林》(抗戰(zhàn)后改名《新園林》)。
在本書里還專門有《蘇州——中國市民大眾文學(xué)的發(fā)源重鎮(zhèn)》 一編,介紹了蘇州籍的10位作家的成就,為他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。當(dāng)然,蘇州籍的通俗作家遠(yuǎn)不止于這10位,范伯群先生表示,他今后還要作進(jìn)一步的努力,將重要的蘇州通俗作家都囊括在他的研究范圍之中。